亏到扛不住!一大批民营医院开始主动“降级求生”了

2025年9月1日清晨,陕西宝鸡眉县的街道还未完全苏醒,眉县槐芽东方医院的门前已围了一圈人。白底红字的“二级综合医院”招牌被缓缓取下,工人踮脚安装最后一颗螺丝后,新制作的“一级综合医院”招牌将取而代之。
“拆了也好,省得看着闹心。”法人代表张立明站在台阶上,听到有人在一旁窃窃私语,神色越发沉重。
这家2018年成立的民营医院,曾在当地 “小有名气”:150张床位(含38张带独立卫浴的高档病床)、引进过CT机、聘请过三甲医院退休专家,甚至连门诊大厅都花大价钱翻新过。
但如今,它缩成了70张床位的一级医院,高档病房改成了普通病房,CT机被传因维护费太高将被转卖,刚招聘进来人才纷纷离职,寻求更好的出路。
“不是不想往上走,是撑不下去了。”医院内部人士向39深呼吸透露,“每年光设备维护费就要掏出百万,人力成本更是压得喘不过气,医院有中高级以上职称的人员高达30名,每人月薪都不是一个小数目,现在降了一级,设备标准降了,高级职称人员也要优化,一年能省小百万。”
其实,眉县槐芽东方医院的“降级”,不是孤例。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民营医院掀起了主动“降级潮”。有的从二级降到一级,有的从一级降成门诊部,甚至一些三级医院也自愿加入了这场“降级运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更高的“医院等级”曾是民营医院追逐的“金字招牌”,为何如今却成了“烫手山芋”?
民营医院的“集体自救”,不是认输是求生
据39深呼吸了解,此次“降级潮”中基本上都是民营医疗机构,它们地域不同,规模各异,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往下走”,主动缩减床位、设备和人员。它折射的,是全国民营医院近年来面临的 “生存大考”。
在陕西宝鸡,另一家二级民营医院——高新中医医院也在今年的5月8日降为一级中医医院。
这家医院成立于2017年,主打“中医理疗”,曾花费巨资引起了高端的中医药设备,床位数也从50张扩张到80张,甚至请过省级中医院专家坐诊。但近年来,它的中医治疗等项目被公立医院“平替”,患者更愿意去离家5公里的市中医院(医保报销比例高5%)。“我们的设备利用率不到30%,每月光维护费就要2万,成了‘吞钱机器’。”
医院员工说,“自从降级后,医院只留基础理疗设备,床位缩到20张,反而能集中精力做社区老年人的推拿、敷贴——这些是公立医院顾不上的‘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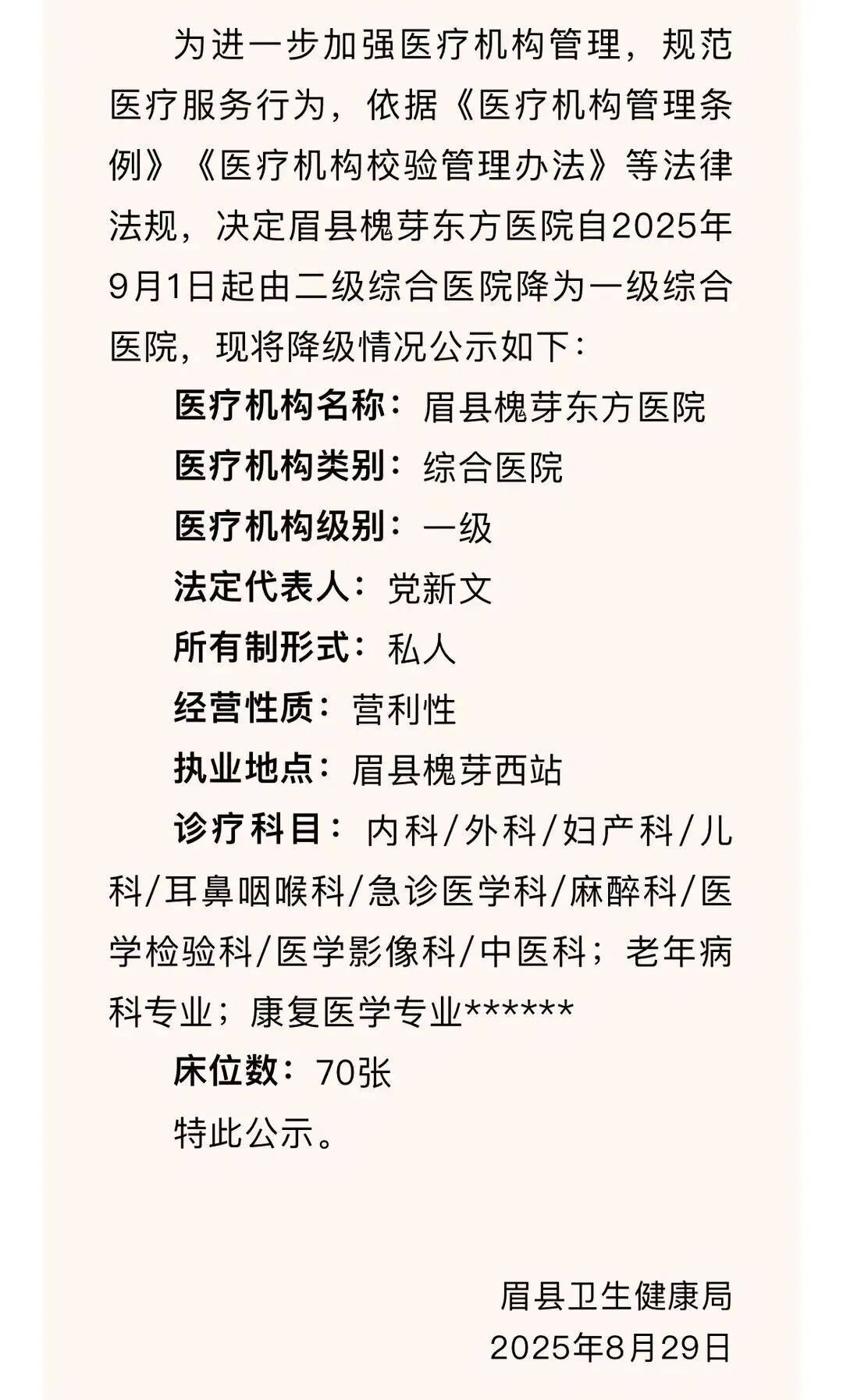
◎ 近期,医疗圈掀起了一股令人意外的“降级潮”。/ 图:健康梅县公众号截图
最让人意外的是,这股“降级潮”甚至波及到了三级医院。
四川乐山华城耳鼻喉医院,曾是当地唯一的三级耳鼻喉专科医院,编制床位120张,建筑面积超1万平方米,却也在成立不久后主动申请降为二级医院,理由直白,“三级医院的设备标准太高,还必须养至少5名副主任医师。可我们的患者70%是普通鼻炎、中耳炎,根本用不上那些高端设备。”
原医院内部人士透露,“降级后,患者觉得‘三级变二级,水平肯定降’,更愿意去市人民医院(三甲)的耳鼻喉科;医生也留不住——年轻医生想去三甲进修,骨干医生被公立医院挖走了。最后,连门诊量都撑不起来。”
“这轮降级潮,本质是民营医院在政策、市场双重挤压下的‘生存策略调整’。”医疗行业分析师王磊向39深呼吸表示,“过去,民营医院追求‘高等级’,是因为等级越高,医保额度越高、患者信任度越强;但现在,高等级的‘成本陷阱’越来越明显——二级医院需要配CT、MRI,三级医院要配PET-CT,这些设备的采购和维护成本,远超民营医院的承受能力。而DRG/DIP支付改革后,医保按病种打包付费,过度检查、治疗的‘灰色利润’没了,民营医院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到‘生死线’。”
39深呼吸发现,此次降级的眉县槐芽东方医院,在2023年11月,因虚构医疗服务项目、串换诊疗项目、过度检查被眉县医保局处罚10万元。
多重压力“绞杀”,40%民营医院“亏本硬撑”
根据国家卫健委及地方卫健委披露的数据,2024年至2025年4月,全国已有多家医院因运营困难或政策调整宣布倒闭或停业,其中民营医院占比85%。
成本、竞争、利润以及监管政策变严等因素,使得一些原本定位为二级甚至三级专科医院的民营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定位,选择降级以求生存。
根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一家二级医院需至少配备100张床位、1台CT机、5名副主任医师;三级医院需至少500张床位、1台MRI机、10名副主任医师。这些“硬指标”,对民营医院来说,是“烧钱游戏”。
“现在很多二级民营医院,年营收刚好卡在800-1000万,利润薄如纸。”某民营医院财务总监赵敏(化名)透露,“更可怕的是,设备越高端,闲置率越高,因为患者不需要,或者医保不让多做检查。比如我们医院的MRI机,月均扫描量不到20次,年折旧150万,相当于每次扫描亏7.5万。”
其次,与民营医院的“惨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立医院的“强势”。数据显示,我国公立医院占全国医院总数的30.77%,但贡献了85.2%的诊疗量;民营医院虽占69.23%,诊疗量仅14.8%。
“公立医院‘出身’就有优势,加上公立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比民营医院高5%-10%,这几年,公立医院还在大规模建立分院,患者更不愿意来民营医院看病了。” 赵敏表示,这种虹吸效应,在三四线城市更明显。
比如陕西宝鸡,全市有4家三甲公立医院,12家二级民营医院。2024年数据显示,宝鸡民营医院的平均床位使用率仅58%(公立医院超85%),很多民营医院的病房空着一半,“连打扫卫生的阿姨都比患者多”。
◎ 近年来,国家开始从严查处医院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和欺诈骗保行为。/ 图: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此外,2021年起,我国全面推进DRG(按病种分组付费)和DIP(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医保支付从“按项目收费”变为“按病种打包”。这对依赖“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盈利的民营医院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
“以前,一个普通感冒,我们可以开1000元的检查(血常规、CRP、胸片),加上500元的药,患者自费300元,医院赚700元。”一家民营医院院长向39深呼吸透露, “现在,DRG规定感冒的总支付价是400元(含检查、药、治疗),如果医院花了500元,多出来的100元就得自己兜着。”
有数据显示,DRG/DIP改革后,民营医院的平均利润率从11.3%暴跌至5.7%;2024年,行业亏损面达40%,平均每家亏损超500万元。疫情后,更有2000多家民营医院破产倒闭——仅2024年,全国医院破产清算案件就有1158件,2025年前7月达766件。
39深呼吸还注意到,一些主动降级的,很多是当初被“认定”了等级但没经过严格评审的机构。2025年7月1日起,国家卫健委医疗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正式启动,二级以上医院为核心督查范围。
整治结果与医院等级评审、医保支付挂钩,质量不达标的医院可能面临评级下降、医保处罚等后果。行业人士表示,主动降级,某种程度上是降低监管风险。
降级之后转型才是“生存密码”,有人活,有人死
降级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成本压力,但显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四川乐山华城耳鼻喉医院在降级后,2024年5月份最终宣告破产。
医疗政策研究专家陈芳指出,“降级只是‘止血’,要让‘血’重新流起来,必须转型。”
据39深呼吸了解,2011年,南京率先尝试将主城区的二级医院,转型为以公益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财政由政府托底。
类似的故事,正在全国上演,广州市海珠区第二人民医院(二级)变为沙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全国100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广州南沙区第一人民医院(原二甲)2024年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整合后,诊疗量反增35%。
除此之外,不久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医养结合示范项目工作方案(2025年版)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引导支持部分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康复医院、护理院。
湘潭市第六人民医院就是这条路径的受益者。该院前身为职工疗养院,转型综合医院后,运营举步维艰。2009年包括退休职工,全院在编256人,但年业务收入只有295万元,就连院长看了账目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即便医院零成本运营,也难以足额发放职工工资。”
此后,随着该院率先在全国公立医院中提出并推进“医疗+养老”服务模式,相继建成了老年养护楼和康复大楼。截至2020年,医院现有床位1100张,其中医养结合床位 800 张,常年入住率超过 95%。仅2019 年一年业务收入就超过1亿元。

◎ 二级医院转型的路子,对民营医院来说,能真正走通的不多。/ 图:全景视觉
但行业人士也表示,对于医院来说,医养结合转型只是一份“参考答案”,不是“唯一答案”。
更关键的是,转型成康复或医养型医院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是二级专科医院,如妇产医院、烧伤医院等,他们转型的成本就更大,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愿意放弃原专业,全部去做全科医生。
江西省瑞昌六二一四医院就是一个例子。此前这家医院同样尝试过医养结合路径,于2018年3月就开设了医养结合型养老院, 2025年2月27日因“亏损严重”正式终止运营,最终仍不能逆转倒闭的命运。
“现在不少二级医院都在尝试开展特定病种服务,在自己的优势专科上发力,避免与大型公立医院正面竞争。“一位来自广东某二级民营医院的投资人告诉39深呼吸,不少二级医院在降级后,依托一级医院资质申请互联网医院。“现在很多门诊部或一级医院都在走这样的路径,通过线上渠道拓展线上诊疗和药品销售,也是个风口。”
不少行业人士指出,未来的民营医院,不要再执着于“二级”“三级”的牌子,而是深耕“患者需要、我们擅长”的领域。毕竟,能让患者愿意走进来、留得住、口碑传出去的医院,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医院。
毕竟,医疗的本质,从来不是“等级”,而是“治愈”。
作者|王慧明
排版|深深
封面|全景视觉
首图|123r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