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名家解读汇编——第56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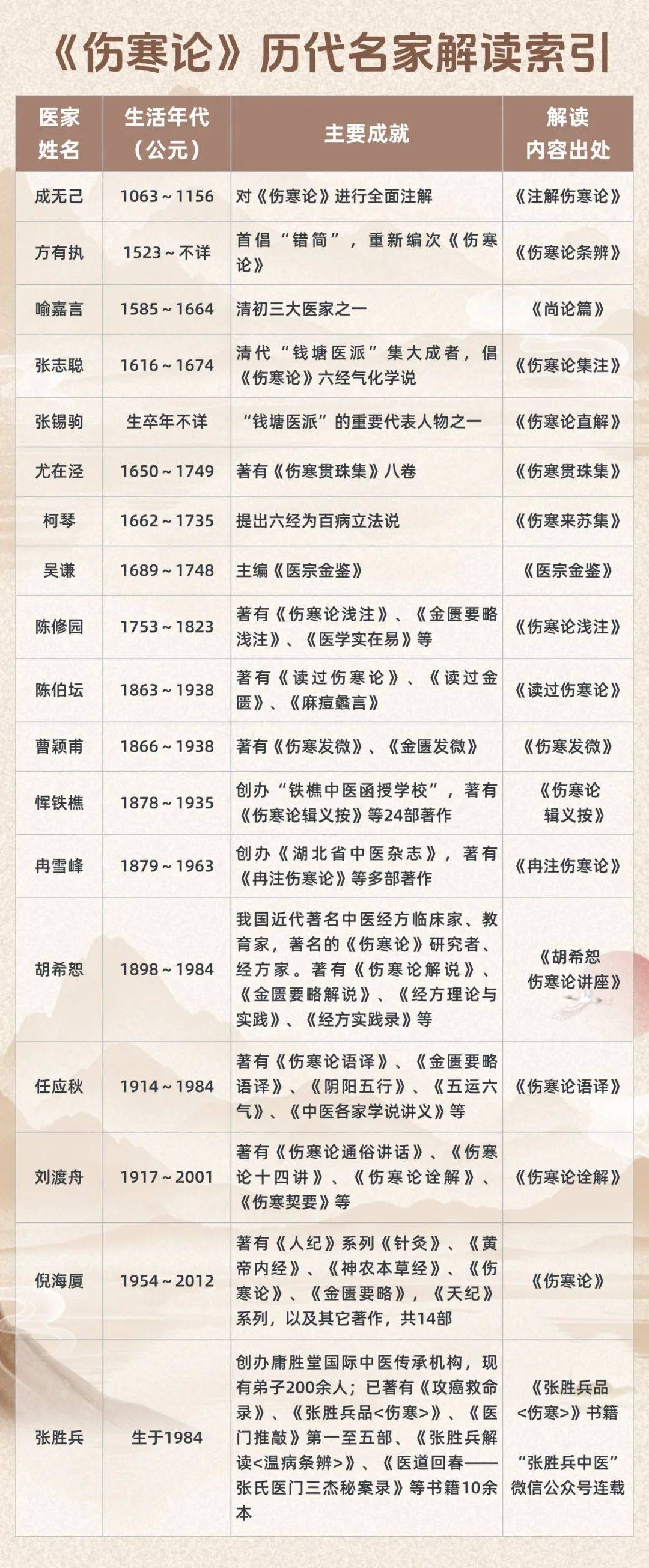
第56条: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故宜当下。若小便清者,知里无热,则不可下。经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况此不大便六七日,小便清者,不可责邪在里,是仍在表也,与桂枝汤以解外。若头疼不已,为表不罢,郁甚于经,迫血妄行,上为衄也。


方有执《伤寒论条辨》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有热则不大便为里实明矣,故虽头痛亦宜承气汤下之。小便清则里无热可知,故曰仍在表宜发汗。然小便清而头痛,阳邪上盛也。故衄可必,而宜桂枝汤解之。承气汤有四方,此不明言,要当随证辨用耳。桂枝汤方见上篇。


喻嘉言《尚论篇》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六七日不大便,明系里热,况有热以证之,更可无疑, 故虽头痛,可用承气下之。若小便清者,邪未入里,即不可下,仍当发汗,以散表邪。然头疼有热,多是风邪上壅,势减必致衄。若兼寒邪,则必如第三项之身疼痛、目瞑,何以但头痛而无身目之证耶?故惟用桂枝汤以解风邪,与用麻黄汤作专之法各别也。


张志聪《伤寒论集注》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此论承气之上承热气,以明头痛有在上、在表、在经之不同。伤寒不大便六七日,热邪内乘也。头痛者,病太阳之在上也。有热者,里有热也。夫承气者,乃承在上之热气而使之下泄,头痛有热,故可与承气汤。其头痛而小便清者,知热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发汗不已而复头痛者,太阳高表之邪入于经脉,故必衄,宜桂枝汤。言头痛有在上、在表、在经之不同者如此。张氏曰∶"当须发汗,宜麻黄汤。"鲁氏曰∶"本论中凡言不大便几日,止论大便之日期,非关六气之日期也。


张锡驹《伤寒论直解》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注】此明头痛有在里在表在经之不同也。不大便六七日,热在里也;头痛有热者,热甚于里,而上乘于头也。与承气汤,上承热气于下,以泄其里热。其头痛而小便清者,知热不在里而在表也,当须发汗以泄其表热。不但此也,又有肌腠之热不解,入于经络而头痛者,必迫血妄行而为衄,仍宜桂枝汤以解肌中之热。
魏子干问曰:热甚于经,何以反用桂枝?答曰:此肌腠之热不解而干于经络,衄则经络之热随血散,然头痛未止,故仍宜桂枝以解肌中之余热,非解络也。


尤在泾《伤寒贯珠集》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太阳风寒外束,令人头痛;阳明热气上冲,亦令人头痛。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证者,知其热盛于里,而气蒸于上,非风寒在表之谓矣,故可与承气汤下之。然热盛于里者,其小便必短赤。若小便清者,知其热不在于里,而仍在于表,当以桂枝汤发其汗,而不可以承气汤攻其里也。若头痛不除者,热留于经,必发鼻衄。"宜桂枝汤"四字,疑在"当须发汗"句下。此条从太阳篇中移入。


柯琴《伤寒来苏集》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此辨太阳阳明之法也。太阳主表,头痛为主;阳明主里,不大便为主。然阳明亦有头痛者,浊气上冲也;太阳亦有不大便者,阳气太重也。六七日是解病之期,七日来仍不大便,病为在里,则头痛身热属阳明。外不解由于内不通也,下之里和而表自解矣。若大便自去,则头痛身热,病为在表仍是太阳,宜桂枝汗之。若汗后热退而头痛不除,阳邪盛于阳位也,阳络受伤,故知必衄,衄乃解矣。本条当有汗出症,故合用桂枝、承气。"有热",当作"身热"。大便圃,从宋本订正,恰合不大便句。见他本作"小便清者",谬。宜桂枝句,直接发汗来,不是用桂枝止衄,亦非用在已衄后也。读者勿以词害义可耳。


吴谦《医宗金鉴》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按〕若头痛之“若”字,当是“苦”字。苦头痛,方为必衄之证。若是“若”字,则凡头痛皆能致衄矣。
〔注〕伤寒不大便六七日,里已实,似可下也。头痛热未已,表未罢,可汗也。然欲下则有头痛发热之表,欲汗则有不大便之里,值此两难之时,惟当以小便辨之。其小便浑赤,是热已在里,即有头痛发热之表,亦属里热,与承气汤下之可也;若小便清白,是热尚在表也,即有不大便之里,仍属表邪,宜以桂枝汤解之。然伤寒头痛不论表里,若苦头痛者,是热剧于荣,故必作衄,衄则荣热解矣。方其未衄之时,无汗宜麻黄汤,有汗宜桂枝汤汗之,则不衄而解矣。
〔集注〕汪琥曰:头痛不已者,为风寒之邪上壅,热甚于经,势必致衄。须乘其未衄之时,酌用麻黄汤或桂枝汤以汗解之。而验小便,实为仲景妙法。
魏荔彤曰:此条之衄,乃意料之辞,非已见之证也。


陈修园《伤寒论浅注》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注】以上两言得衄而解,又言得衄而仍不解,大旨以汗之与血异名同类,不从汗解,必从衄解。既衄而不成衄者,又当从汗而解之,言之详矣,然衄证又当以头痛为提纲,以头为诸阳之会。督脉与太阳同起于目内眦,邪热盛则起于督脉而为衄也。
然头痛病在上也,而察其病机则在于下:一曰大便,一曰小便。若伤寒不大便六日,六经之气已周七日又值太阳主气之期,头痛有热者,热盛于里,而上乘于头,与承气汤,上承热气于下,以泄其里热。
其头痛有热而小便清者,知热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以麻黄汤泄其表热。此一表一里之证,俱见头痛。
若头痛不已者,势必逼血上行而为衄,此可于未衄之前,以头痛而预定之也。
然犹有言之耒尽者,病在表者固宜麻黄汤,至于病在肌腠,其邪热从肌腠而入经络,头痛亦必作衄,宜以桂枝汤于未备之前而解之。
此一节以“头痛者必衄”五字为主,而言在里、在表、在经之不同,欲学者一隅而三反也。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本条又病在表,发汗偏宜桂枝矣。异在伤寒而表证不一具,只有与中风同具之头痛。尤异在不大便六七日,且有在里之端倪。独是六七日不更衣无所苦,所苦者但头痛,又何庸理会其大便乎?惟不大便可以征明其有热,下文过经有热曰大便当鞭,卒主调胃承气者。以内实故,特彼证有热则请语,吾知其在里不在表。本证有热无谵语,亦预知其在表不在里矣,似无与承气之必要也。曰与承气汤,太阳病无行大小承气之例,与调胃承气不待言,欲验明其热不待言。曰其小便清者,殆指小便无热色,便知大便无热邪,故曰知不在里仍在表,犹云热不在阳明在太阳,一若划清太阳阳明之病所也者。岂知阳明有热不头痛,头痛必手足厥,不厥则证非阳明已大白,遑执小便之清不清,为在表在里之标准乎?夫太阳表证不胜书,未有云小便清也。阳明里证不胜书,未有云小便不清也。况热则就如病在表,几见有人小便清乎?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往往小便非热尿色热,尿色与皮毛,有息息相通之故也。然则与汤是何作用耶?非为不大便行承气,为头痛行承气。玩其字清字,可悟长沙之手眼矣。头者精明之府也,痛则有之,非热邪能集矢也。盖有胃脉提举阳明清肃之气,上加于头,其头遂日戴清阳之覆帱而自若,热至则似有似无者也。若六七日不大便,又非所论于胃脉之常。倘精阳气或缺于奉上,则头部无保障。恐不特太阳移其痛于头,并移热于头,是病在头,太阳转作无热论矣。以其头痛不发热,可疑处是太阳之头有热,非太阳之身有热故也,安得不与承气以观其后乎?既于小便得其信息,对于大便自得其真情,便想见阳明方为太阳忙,从交頞中旁约太阳之脉。六七日令热邪不得逞者,乃阳明争回其头部,以为之宰也,何暇传道其变化乎?不大便于热状无增减,度亦清升而浊未降耳。一旦以承气拨动其下之浊者,旋降下其上之清者,岂同小便色白热已除哉?乃清空之宇,非余热所能淆,知热不在头部,仍在太阳也。易其词曰表曰里者,表里是通称两方面之词,非太阳阳明之定称也。太阳在表,头即其里也。曰当须发汗,表证当发汗。痛处有热,余处不痛不热,则急须发汗。不发汗将致衄,麻黄汤不可少矣乎,致衄又无头痛也。上文所有头痛无衄状,大都头痛未必衄。本证又不衄头不痛,若头痛者必衄,伤寒发于阴也。足太阳从阴经上逆于头,壅遏其血,遂稽留其热,痛在是即热在是,衄亦在是。其所以未衄者,经未尽耳,苟非发汗,热邪肯别血以出乎?麻黄又微嫌夺血也。曰宜桂枝汤,宁取汗于卫,不取汗于营,乘其经血之更新,迎导足太阳之热,向手太阳去,头畅则不衄矣,不衄无不大便矣,未衄以前用桂枝,对上既衄之后用麻黄。举汗字衄字了清麻桂之首尾,无非一表字外字解字发字先清麻桂之眉目。权衡麻桂处,正分寸麻桂处也。


曹颖甫《伤寒发微》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已及再经之期,病邪将传阳明。六七日不大便而见头痛发热,则已见阳明之证,但阳明头痛与太阳异,太阳之头痛,在额旁太阳穴,阳明头痛在阙上。两眉间曰阙,属阳明。病传阳明,故阙上痛,痛则可与承气汤。惟大肠燥热,必蕴蒸输尿管及膀胱,而小便赤痛。若小便清者,则肠中无热,病邪尚在皮毛,便当用麻黄汤以发皮毛之汗,以病在肺与皮毛,太阳寒水用事,故小便清也。若太阳标热太盛,上冲于脑,则阙上或连太阳穴痛。颅骨之缝,以得热而开,必将血流鼻孔而成衄,故“头痛者必衄”。所以然者,以腠理不开,而郁热上冒也。用桂枝汤以发肌理之汗,则汗一出而衄自止矣。


恽铁樵《伤寒论辑义按》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玉函》作” 未可与承 气汤”,是。“其小便清者”,《玉函》《外台》并作“小便反清”,《脉经》《千金翼》作“大便反清”,柯本作” 大便圊”。“知”,《玉函》《脉经》《千金翼》作” 此为” 二字。王肯堂校本、《千金翼》“有热” 作” 身热”,“热” 后有” 小便赤” 三字,“其小便清” 作“若小便利”。
成无己云: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故宜当下。若小便清者,知里无热,则不可下。经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况此不大便六七日,小便清者,不可责邪在里,是仍在表也,与桂枝汤以解外。若头痛不已,为表不罢,郁甚于经,迫血妄行,上为衄也。
程应旄云:欲攻里,则有头痛之表证可疑;欲解表,则有不大便之里证可疑。表里之间,何从辨之?以热辨之而已。热之有无,何从辨之?以小便辨之而已。有热者,小便必短赤,热已入里,头痛只属热壅,可以攻里。其小便清者,无热可知,热未入里,不大便只属风秘,仍须发汗。
汪琥云:若头痛不已者,为风寒之邪上壅,热甚于经,势必致衄。须乘其未衄之时,宜用桂枝汤,以汗解之。
周扬俊云:此因发汗之后,不得再用麻黄也。
魏荔彤云:此条之衄,意料之辞,非已见之证。用桂枝汤则可不衄而解,与用麻黄汤一条亦有别。
丹波元简云:《伤寒选录》云:丹溪曰:谨按外证未解不可下,下为逆。今头痛有热,宜解表,反与承气,正是责其妄下之过也。故下文又言“小便清者,知其无里邪,不当行承气”,又继之曰“当须发汗”,曰“头痛必衄血,宜桂枝汤”,反复告戒,论意甚明。而注反直曰“故当宜下”,想因六七日不大便尔。虽不大便,他无所苦,候表解然后攻之,正仲景法也,注意似未莹。按此说,与《玉函》相符矣。
又云:《伤寒类方》云: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宜下之候。头痛有热者,未可与承气汤,太阳症仍在,不得以日久不便而下也。按“未可”二字,从《金匮》增入,《伤寒论》失此二字。又按:徐氏注解近是,故表而出焉。又按:张志聪发汗用麻黄汤,柯氏改“小便清”作“大便圊”,并非也。
铁樵按:此条与前第五十一条“二阳并病”,及第三十二条“问曰:证象阳旦”文字皆不甚顺,皆不可凿解。吾人于大纲研究明白,小节纵有错讹,亦不致胸无主宰,此读书但观大略之所以可贵。若桂枝节节以为之,则此等处,皆足为大障碍矣。本条既是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别无其他里证,自与承气无关,可知“与承气汤”句之上下文,必尚有讹误。又细绎“若头痛者必衄”句,于上文亦不甚允洽。且据本条见证,无论如何释,苟见头痛,亦未见衄之可必,此则证之实验而知本文必有讹误也。伤寒小便清者,常常遇之,其证确是里寒,万不可用承气攻下。亦有溲清由于肺热者,非一表可以济事,则首句“伤寒”字须着眼。盖无汗发热头痛,小便清者,宜发表。若有汗热不解,渴甚者,乃是肺热,其六七日不大便,必须有腹痛,转矢气,表证已罢者,方可与承气。盖头痛有表证头痛,亦有胃气上逆而头痛,非可执一。是本条大致尚可理会,惟总有阙文耳。


冉雪峰《冉注伤寒论》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冉雪峰曰:此条审度病机出入,以可下证,衬出当汗证,以承气汤,衬出桂枝汤。前三十六条,太阳与阳明合病,和前四十二条,二阳并病,均是太阳涉及阳明,缘太阳与阳明是相递接的。表未罢当顾表,里已急当救里,此是治疗通例。但以上各条,均叙列在太阳篇内,故多归结到太阳从表的方面。本条不大便六七日,似阳明病,头痛有热,似太阳病,要之太阳寒束,可以上折而头痛,阳明热壅,亦可上灼而头痛,是头痛为太阳阳明共有证象。伤寒为热病,太阳遏闭,寒即化热。阳明则纯化热,以故不恶寒,惟发热。今只言热不言寒,义更浑括。是有热亦为太阳阳明共有证象,所以与承气汤。设病的机窍在里,里气化则表气化,必下后濈然汗出而解。若其人大便清,里无燥结,小便清,里无热结,知其关键不在里而在表。在表则汗,在里则下,热逆上则头痛,热不下则便清,热归府则不大便,热动经则必衄血,表里上下内外出入,在府在经,为汗为衄,一气传化,在临证细心辨认。冠首明标伤寒,本宜麻黄汤,而云宜桂枝汤者,此必在六七日中,业经发汗,或病历多日,热化已甚,寒闭渐松,微自有汗,此可见伤寒有转变用桂枝的,不必方用桂枝,即扯向中风去。当须发汗,宜桂枝汤二句,均须活看。当发汗,是言当治表,宜桂枝,是言宜和表,各归其宗,随所攸利,因病制宜,存乎其人。前有太阳病,不发汗,或太阳病,汗出不解各条,缘何不发汗,缘何不解,此必如合病并病,有里证的关连在,但未明言。补此条,则前后贯彻,各各昭然。吾人对经论,必须将同异分别读,又须合前后连贯读。


胡希恕《胡希恕伤寒论讲座》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这一条是表里病情很混淆,“头痛有热”是表里共有的病,太阳病也有头痛发热,阳明病也有头痛发热。原起是伤寒就是表实证,就是无汗的这种伤寒,已经不大便六七天了,那么这个头痛有热大概是里实的问题。久不大便,就造成自己中毒。饮食入胃,血管要吸收。可是老不大便再吸收,就是有了毒素它也吸收,生理上就这个样子,它不知道有毒没毒,所以日久不大便容易有头痛的。六七天不大便,头痛有热,按着常规上看,这是里实证,与承气汤。这个“与承气汤”,也不是说“主之”。这个书,“主之”就是固定不移的。“与之”,比“宜”的口气更轻,“宜”就是当、应当,也不是“主之”。“与”是大有商量余地的,“与承气汤”——承气汤也有多种,大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等——可以与承气汤,就是根据这个病情的轻重缓急,斟酌着用吧,是这个意思。
假若真是里有热,小便要红赤的,这是很要紧的,这是辨证的法子了。头痛有热,不但阳明病有,太阳病也有。如果是阳明病,它里热,里热了小便红赤。“小便清者”,色不变,“知不在里,仍在表”,这种情况虽然六七天不大便,你不要光看不大便,这还是表证,要是阳明病,小便绝对变色。“当须发汗”,那么这种情况还是要发汗的。
这就是病有疑似之间,我们找特别的鉴别方法,尤其表热、里热鉴别的方法,以小便是最好辨了,所以咱们在临床上要问,不问不行。当然他也是举这么一个例子,脉也有问题啊。如果是表证,脉准浮。如果是里证,脉绝不那样子浮,或者要沉。这是让你辨证的时候,抓主要的关键(的症状)。表热里热,最容易辨的莫过于小便,你问问小便怎么样,小便一点颜色也不变的,里头没有热,你就别给人吃承气汤了,这还仍在表,当须发汗。这个发汗,可能它是用麻黄汤。他说的是发汗,而且开始他用的是伤寒(的说法),没有汗。
“若头痛者,必衄”,这一句话差不多就是一段的意思。假若吃过麻黄汤发汗,而头痛不已,那个人必衄,什么道理呢?这就是病深,病在六七天,热病都往上冲,六七天发汗之后还不好,脑袋还疼,说明上冲也厉害,上冲是桂枝汤的主要症状,所以治头痛麻黄汤不如桂枝汤。可是麻黄汤也有桂枝,但是桂枝量也小,所以一般的头痛大概用桂枝汤的多。无汗,你不能吃桂枝汤,先要吃麻黄汤,可吃了,头痛还仍然不好,就是与桂枝证上冲有关,不但头不好,而且必衄。“宜桂枝汤”,这个时候应该用桂枝汤再小发汗就好了。
这条也挺重要,重要在哪儿呢?就在验其小便以知表里。汗下异法啊,这很重要,该发汗的吃泻药不行,真正阳明病发汗也不行,越发汗,里头热结得越厉害。假若发汗不好,脑袋疼得厉害,鼻子出血,你以为解表解错了?也不是的。那是因为久不得汗出,阳气重是一方面,同时(另一方面是)气冲得也厉害,气往上冲,这时候你再更发汗,因为表还是没解。


任应秋《伤寒论语译》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校勘】《玉函经》:作“未可与承气汤”。《玉函经》《外台秘要》:“其小便清者”句,作“小便反清”。《脉经》《千金翼方》:“其小便清者”句,作“大便反青”。《脉经》《玉函经》《千金翼方》“知”字作“此为”二字。王肯堂校本《千金翼方》:“有热”作“身热”;“热”字下有“小便赤”三字;“其小便清”作“若小便利”。
【串解】成无己云:“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故宜当下,若小便清者,知里无热,则不可下,经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况此不大便六七日,小便清者,不可责邪在里,是仍在表也,与桂枝汤以解外,若头疼不已,为表不罢,郁甚于经,迫血妄行,上为衄也。”
胃肠病往往会引起脑症状,如六七天不解大便,便会自家中毒,发生头痛。而高热不退和大便不解,亦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时最好用大承气汤通便,大便通畅了,头痛发热,同时减退,这是临床上屡试不爽的经验。“小便清”,是无里热,也就是正气抗病的趋势并没有向里向下,应当用桂枝汤解表,但仍应服于未衄以前。
【语译】患太阳伤寒证,发热头痛,但已经六七天不解大便了,便应该服承气汤泻下剂,减轻它的自家中毒。假如它这时小便很清畅,就说明并不是里热证,仍然是表证的发热头痛,即行用桂枝汤解表。如表证长期不解,不断地头部充血,不仅头痛一时好不了,甚而还会引起衄血的。


刘渡舟《伤寒论诠解》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解析】本条通过小便的清与赤以辨表里,并论述表里的不同证治。“伤寒”在此泛指外感热病。在外感热病的发病过程中,六七日不大便,又见头痛有热。此处不具体说翕翕发热,还是蒸蒸发热,或是日晡潮热,是为进一步辨证留有余地。从“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一句可知病仍在表,如头痛有热属于阳明里热上熏的,其小便必黄赤,其发热必蒸蒸或潮热,治疗自当用承气汤泻下。今小便清,则知里无燥热,病邪仍在于表,其证应头项痛、翕翕而热、恶风寒,尽管不大便六七日,因腹部无所苦,也不可用泻下之法,可考虑选用桂枝汤发汗。“宜桂枝汤”,应接“当须发汗”之后。对于太阳经邪不解,头痛日久,阳郁过甚的病人,也可以出现鼻衄代汗自解的情况。
《续名医类案》载李士材治一个患伤寒六日的病人,
谵语狂笑,头痛有汗,大便不通,小便自利,众议承气汤下之。脉之,洪而大,因思仲景云: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小便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方今仲冬,宜与桂枝汤。众皆咋舌掩口,谤甚力,以
谵语为阳盛,桂枝入口必毙矣。李曰:汗多神昏,故发谵妄,虽不大便,腹无所苦,和其营卫,必自愈矣。遂违众议用之。及夜,笑语皆止,明日大便自通。从这一病案看,
谵语狂笑,头痛有汗,大便不通,均似阳明里热可下之证,然小便不短赤而自利,为里无热;脉不沉实而洪大,为里无实,腹无胀满疼痛之苦,为无可下之证。李士材抓住了以上辨证眼目,果断地使用桂枝汤调和营卫以解表,使病得以速愈,可以说是深得仲景的辨证要领,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


倪海厦《伤寒论》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如果人得到伤寒,这病人已经六七天没大便了,气色已经黑了,看他的脸色像有一层灰,没光.整个人很躁这时候病人头痛有热,这头痛已经不是感冒的头痛了.大便不出来的头痛和感冒的头痛不样 两眉的中间这一块是「阙上头痛的时候冈好在印堂这一块痛 就是阙上痛」,就是有便秘,所以头痛痛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就是标准的阳明痛,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阳明经就是在腑的系统里面,大便堵到的时候,肠气冲到头上就是大便的浊气一直上冲,刚好冲到「阙上」这个地方,所以在「印堂」上面有看到红丝就是有痔疮,就给承气汤。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如果大便燥屎,堵在里面的时候,病人的小便一定是黄浊,因为下焦非常的热,所以张仲景在提醒攻大便的时候.要问病人小便是什么颜色?如果小便很清,代表下焦不热,病不在里,还在表,就代表这头痛在表,并不是「阙上痛」,发表用桂枝汤来发,如果不发汗,热上来的时候,一样会造成鼻衄。如果临床上遇到病人有表证,又五六天没大便了,先不考虑里证,承气汤的症状是热实 有执也有实所以承气汤里面有去执的药也有去实的药.,如何知道是寒还是热,看小便,小便白就是寒,小便黄就是热,我们用承气汤,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就是看小便颜色。[大黄]张仲景并没有真正去分寒热 去实一定要加大黄 把去热的药加上大黄,就可以去热实,所以承气汤里面的大黄是去实,黄芩黄连都是去热的药,如果病人是寒实,也是实,也是有东西堵到,但是这个堵到的乃因为肠子不蠕动所以如果是寒让大便堵到不通的,要开去寒的药.让肠胃蠕动恢复功能才行,把去寒的药加上大黄就可以去寒实,譬如细辛、附子都是热的药.这样大便就清出来了。所以处方的时候.要确定到底是寒实还是热实。
张胜兵《张胜兵品伤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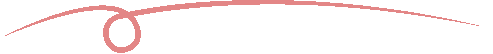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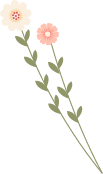
第56条: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以下解读内容为精选版,详细解读请查看:
第40讲张胜兵品《伤寒》之太阳病(55、56条文)
我们先来解析一下这条条文中一些有疑难的字句或词语。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有观点认为这里“小便清”应是“大便清”。但这种说法不太合理。
一方面,张仲景作为一代医圣,不太可能将“大小便”混淆。另一方面,若此处为“大便清”,从文字角度看,也不符合其用词习惯。在第23条中,张仲景提到“清便欲自可”,这里的“清”通“圊”,意为厕所,“清便欲自可”即排便正常。如果第56条是“大便清”,不仅与前文用词习惯不符,在同一本书中出现这样的差异也极为罕见。所以,这里的“其小便清者”指的就是小便清澈。因为如果阳明腑实证有热,小便应该是黄赤的;若小便清澈,说明下焦无热,也就意味着没有里证,即“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
再看后面的“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这里运用了倒装文法,正确的语序应该是“当须发汗,宜桂枝汤;若头痛者,必衄”。
此外,关于“若头痛者,必衄”,有医家将其中的“若”改为“苦”,比如《医宗金鉴》就持此观点。其理由是前文已经提到“头痛有热”,若再用“若头痛者”,就显得重复。但实际上,这种理解有误。这里的“若头痛者,必衄”强调的是服用桂枝汤后仍头痛,并非“苦”的意思。
还有“必衄”这一表述,很多医家将其解释为“一定流鼻血”。然而,这种理解过于肤浅,也误解了张仲景用“必”字的深意。
在第19条中,张仲景说“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这里的“必”并非“一定”的意思,而是“有可能”。同样,在第32条中,“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这里的“必”也应理解为“有可能”。所以,第56条中的“必衄”应解释为“可能会流鼻血”。比如清朝的伤寒大家柯琴在《伤寒来苏集》中将其解释为“一定会流鼻血”,这种理解就不准确。
第56条条文,我们将其翻译如下:外感病,已经六七天不大便,且伴有头痛、发热等症状。如果小便黄赤,说明是阳明里实证,可用承气汤治疗;如果小便清澈,说明内无邪热,病仍在表,应当用发汗法治疗,可用桂枝汤。若头痛、发热等症状持续不解,表邪郁滞较盛,可能会出现流鼻血的症状。
有人说这一条是辨太阳阳明之法,也有人认为是根据小便清否来辨表里。无论如何理解,这一条都涉及表里的辨别。
关于第56条,有几个争议点。一是“小便清”,我们已确定不是“大便清”;二是“若头痛者”,应保持原文,理解为“若头痛者,必衄”;三是“必衄”,应理解为“可能会流鼻血”。
对于“伤寒不大便六七日”中的“伤寒”,不同医家有不同理解。胡希恕胡老认为这里的“伤寒”指太阳伤寒表实证;刘渡舟刘老则认为这里的“伤寒”泛指表证或外感热病。
在《伤寒论》中,出现“中风”“伤寒”等字眼时,很可能都指外感热病或太阳病。因为太阳伤寒表实和太阳中风表虚是后世医家的总结,张仲景并未明确提及。胡老将其理解为太阳伤寒表实证,可能是考虑到大便不通的情况,但后面又有“宜桂枝汤”,所以这种理解可能不太准确。
太阳病外感风寒,六七天不大便,伴有头痛、发热等症状。仅从这些症状看,既可能是太阳表证,也可能是阳明里证。太阳表证的头痛、发热容易理解;阳明里证的头痛、发热则是由于里热结实、腑气不通、胃气不降、灼热上攻所致,同时还会伴有小便黄赤等里热表现。
有人可能会问,太阳表证为何会出现不大便六七日的情况?这是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表邪郁闭于皮毛,肺气不能肃降,进而影响大肠的传导功能,导致大便不通。这种情况在太阳表证中虽非必然症状,但确实可能出现。
邪气在表,出现头痛、发热等症状,小便应清澈。若小便黄赤,则说明有里热,可考虑使用承气汤。但具体使用哪种承气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还是调胃承气汤),需根据具体病情“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若小便清澈,说明无里热,头痛、发热为表热,病仍在表,当须发汗,宜用桂枝汤。由此可推断,前文中的“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应指太阳中风表虚证。因为如果是表实证,张仲景不会用桂枝汤。而且,桂枝汤证也可能出现不大便的情况。
第182条条文提到:“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这说明阳明病在外可能有汗自出的表现,进一步佐证了第56条中的“伤寒”应指桂枝汤证,而非麻黄汤证。
除了从小便清否来判断病在表还是在里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细节辅助判断。比如,阳明里证可能伴有腹胀、腹痛等症状;而太阳病引起的便秘通常不会出现腹胀、腹痛。此外,从发热的表现也可鉴别:邪气在表时为头项胀痛、翕翕发热;阳明病则为蒸蒸发热或潮热。
张仲景在第56条中给出了辨太阳阳明之法的示范,教我们如何鉴别表里证。这里虽重点提到用小便清否来判断,但实际上还可通过腹痛、腹胀及发热表现等辅助判断。我们应掌握这种辨别的方式、方法和思路,达到“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法胜有法”的境界。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电视剧《精武英雄》。霍元甲用武学扬我国威、提高民众自救精神。如今,武学已成娱乐,而医学仍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医学扬我国威的时代正在进行中,我们这一代中医人及新生代中医代表将为医学在全世界范围内扬我国威而继续努力。
在《伤寒论》的学习群里,有很多中医爱好者和医生,他们年纪虽大,但仍坚持学习中医、学好《伤寒论》。看到他们听课后做的笔记,我深受感动。有这么一代人坚持下去,中医何愁不能兴盛蓬勃发展?
正如曹操所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感谢大家一直陪伴我在《伤寒论》的学习之路上。希望在《伤寒论》398条条文讲完后,群里能出一些名医,为中医的发扬光大、传承发展做出贡献。我张胜兵将与大家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