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度抑郁、人格分裂、极端恋爱纠缠了15年后(四)
混沌里的片刻安宁
跟着妈妈学佛的那段日子,是我混沌生活里难得的喘息。
脑子里那些嘈杂的、拉扯的声音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不用再费力纠结过往那些荒唐的事,也不用跟晨曦、曦曦争抢身体的控制权。
我就像个被牵着走的影子,跟在妈妈身后,听着寺院里断断续续的木鱼声,闻着空气中飘着的、淡淡的檀香,心里竟升起一丝久违的平静。这种平静很轻,像一层薄雪,稍碰就会碎,但已经足够让我暂时逃离抑郁症带来的沉重窒息感。
起初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氛围。没有是非,没有异样的眼光,不用怕自己的异常被发现。大家围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读经、分享心得。读书会也好,班修也罢,我缩在角落里,听着他们讲自己的感悟,聊生活里的烦恼和解脱的办法。偶尔我也会插上一两句话,跟他们一起评价那些细碎的道理。
被接纳、能畅所欲言的感觉,像温水裹住冰冷的手脚,是我前半生从未有过的踏实。双相障碍带来的情绪波动,在这段时光里也平缓了许多,我甚至开始偷偷期待,或许佛法能治好我心里的病。
在这份微弱的期待里,我鼓起全身的勇气,跟妈妈说想正式进班进修。可真正走进班级,才发现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进班第一天,我认识了Mandy。
她性格很温和,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对佛法的理解也很通透,不像其他人那样带着距离感。我们很快成了朋友,课上一起记笔记、讨论经文里的意思,课下她会鼓励我,陪我一起精进修行。
那段日子,我偶尔能感觉到纯粹的快乐,像黑暗里透进来的一点点光,让我暂时忘了重度抑郁症和双相障碍的折磨。可这份快乐没持续多久,Mandy就换了修行线路,去了其他寺院做长期居士,我又成了孤单一人。

孤单里的难堪与窒息
Mandy走后,孤独感还没完全漫上来,辅导员的排挤就先到了。
那天共修分享,我攥着衣角,反复深呼吸了好几次,才鼓起勇气开口。刚说了两句自己对“放下执念”的粗浅理解,辅导员就抱着胳膊打断了我。她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笑,声音不算大,却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你这理解太浅了,没沉下心来悟,怕是心思还在别处吧?”
话音刚落,周围就传来几声窃窃私语。
我的脸一下子烧得通红,攥着衣角的手指用力到泛白,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抑郁症的自卑和羞耻感翻涌上来,让我恨不得立刻消失。
之后的共修,排挤变得更明显了。每次大家在座位上轮流分享,辅导员的目光总会跳过我,先点其他人发言。就算轮到我,她也会全程皱着眉,要么低头翻书不看我,要么没等我说完就打断。
有同学悄悄告诉我,辅导员私下跟她们说我“经历太复杂,心不诚,不适合深修”。
那些轻飘飘的话,像无数根细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心里。那种被孤立的难堪,和大学时被同学议论、被男生疏远的滋味一模一样,双相障碍的躁期好像要被触发了。
我心里又慌又乱,却又被重度抑郁的无力感捆着,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我坐在教室里的每一秒都像在受刑,浑身不自在,只想逃。

洛辰的反击与失控
辅导员的排挤像一把钥匙,撬开了我记忆里所有被孤立的片段。憋闷、无助、委屈,这些情绪堵在胸口,让我喘不上气。就在这时,一股陌生的、带着戾气的劲儿突然从意识深处冒了出来——是洛辰,一个全新的、叛逆的男孩子人格。
他不像我这样懦弱,满脑子都是不服输的小聪明,他带着股痞气。他嫌我太窝囊,嫌我分享的内容太老实、太憋屈,在我脑子里嗤笑:“怂什么?他们看不起你,你就给他们好看。”
我还没反应过来,指尖就不受控制地打开了手机浏览器,噼里啪啦搜起了“佛学修学心得分享”。
我慌了神,在意识里尖叫、挣扎:“别这样,会被发现的!我们好好学不行吗?” 洛辰根本不理我,只带着玩世不恭的调子说:“好好学?他们给你机会了吗?他们就喜欢听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咱给他们演一场就是了。”
他飞快地扒拉着别人的分享稿,挑了几段写得漂亮的话,改了改人称,就复制粘贴到我的文档里。
轮到我在座位上分享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嘴角不受控制地勾起一抹痞气的笑,声音也比平时粗了几分。那些根本不是我经历的感受,像流水一样从嘴里说出来,什么“观照自身杂念,方能破除烦恼障”,什么“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听得周围人频频点头。
我急得在意识里拼命捶打、嘶吼:“快停下!这不是我们的话!会被赶出去的!” 可洛辰充耳不闻,甚至还故意加了几句自己编的“感悟”,调子扬得高高的,特意朝着辅导员的方向说,像在挑衅。
辅导员的眉头越皱越紧,眼神里的不满几乎要溢出来。
辅导员果然当众点名警告我:“分享要发自内心,要照着书上的要义结合自己的实际,不能拿别人的案例往自己身上套。”
她的声音冷冰冰的,带着不耐烦。可洛辰根本不在意,下次分享依旧我行我素,梗着脖子把改好的稿子念得铿锵有力。终于,在又一次“标新立异”的分享后,辅导员忍无可忍,当着全班人的面,冷冰冰地把我赶出了三级修学。
那一刻,我能感觉到洛辰在意识里冷哼一声,满是不屑和挑衅后的快意。而我,只剩下一片麻木的疲惫。抑郁症的沉重感瞬间把我淹没,双相障碍的情绪波动也跟着袭来,心里又空又痛,却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我知道洛辰是想替我反抗,可他不知道,这样的反抗,只让我在混乱的边缘又坠深了一分。
分享结束后,我浑身都在发抖,洛辰还在意识里吹着口哨,满不在乎地说:“瞧,这不比你吭吭哧哧说那些真心话强?”
我沉默着,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只觉得自己像个被抽线的木偶,连痛苦都变得麻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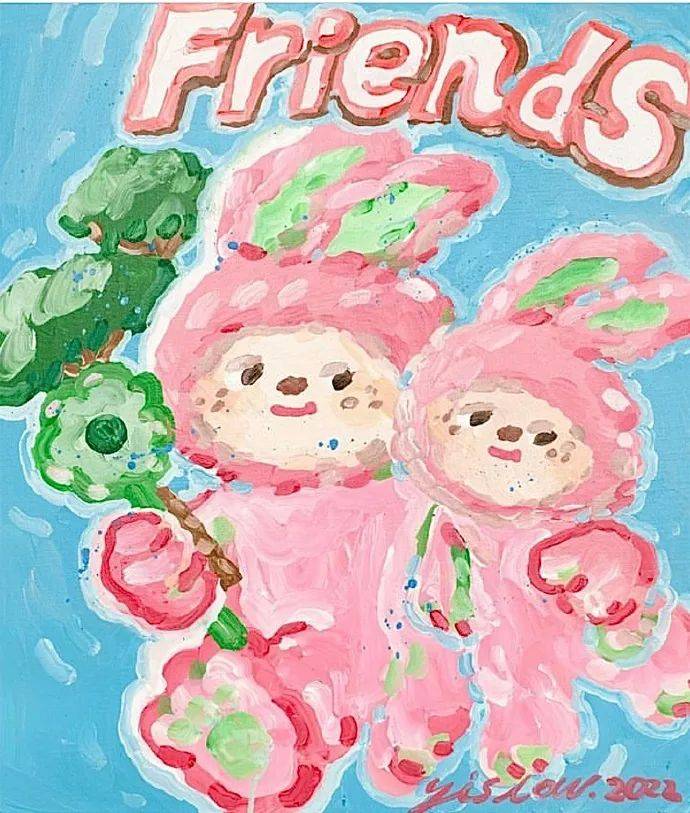
又一场失控的虚假恋爱
修学半年左右,平静还没来得及稳住,又一件不受控制的事砸了过来。
班级里有位长者,平时话不多,却总爱打量我。某天共修结束后,她特意拦住我,说要给我介绍她的外甥,还说“你们年纪相仿,聊聊看,说不定能处成男女朋友”。我站在原地,脑子嗡嗡作响,抑郁症带来的迟钝感让我连拒绝或同意的反应都做不出来,只能愣着发呆。
我还没来得及组织语言,意识里就传来曦曦的声音,带着点雀跃的调子:“好啊,那就聊聊看。” 我还没反应过来,嘴里就已经说出了和曦曦想法一样的话。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和那个素不相识的男生在一起了,这段由曦曦主导的关系,一晃就持续了半年。
回望这半年与JZH相伴的时光,所谓恋爱,不过是他精心编排的一场深情独角戏。
被重度抑郁症纠缠的第十四个年头,双相障碍的情绪浪潮反复冲刷,早已磨平了我对感情的所有期许。可当他递来那份看似真挚的心意时,我竟鬼使神差地选择了配合。
这或许是因为长期蜷缩在情绪牢笼里,太需要一个虚假的出口呼吸,或许是因为想借一段新的羁绊,稀释XXL曾给予的沉重温柔,那份好重到让我不敢回望,只能拼命逃离。
JZH把自己塑造成满心满眼都是我的模样,用细致的关怀、温柔的言辞,让周遭人都深信他爱我至深,反倒是我淡漠疏离,不懂珍惜。可那些刻意堆砌的深情,在我因双相而敏感的神经里,早已破绽百出。
我太累了,累到懒得戳破,便顺着他的剧本,扮演起一个沉溺其中的“恋爱脑”。我比他更投入地演绎着炽热,让所有人都以为我早已离不开他,只有我自己清楚,这份“爱”里,全是麻木的敷衍。
躁期时的情绪亢奋,让我能精准拿捏每一份“深情”的分寸;抑郁期的心如死灰,又让我能隔着一层薄纱,冷眼旁观这场闹剧的起承转合。
他那些自以为天衣无缝的破绽,我都看在眼里,却从未点破:他总回避视频通话,每次我提起,都能被他用各种理由轻轻带过;语音时偶尔传来的陌生女声,我假装未曾察觉;他让我翻看相册找照片时,那些精心雕琢的自拍照,明晃晃地透着不专属的痕迹,我也只是匆匆扫过,不作声张。
我就像一个沉默的观众,看着他在舞台上独自演绎着专情,心里没有波澜,只有一片荒芜。
真正让我演不下去的,是他踩过了我的底线。
在我最亲近的亲人离世,我被悲伤与病情双重裹挟、摇摇欲坠时,他竟提出了过分的要求。那一刻,我对他所有的敷衍都烟消云散,只剩下生理性的恶心与心寒。还有我生日那天,他在我家煮了一碗清汤面,连个鸡蛋都没有,却还轻描淡写地说着“为我好”。
那些日子里,他用隐晦的PUA裹挟我,甚至用极端的方式逼我妥协,让我本就脆弱的情绪雪上加霜。可我还是忍了,继续扮演着那个离不开他的角色,不是舍不得,只是没力气再掀起一场新的风波。
JZH永远不会知道,我早就把他对我做的事告诉了XXL。4月18日的钢琴房门口,XXL提着铁棒站在那里,眼底的怒火几乎要溢出来。XXL对我的爱,从来带着极端的偏执,他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份虚假的深情靠近我?是我无意间的引导,让JZH那些刻意伪装的细节,完整地暴露在XXL眼前。
最后XXL没有动手,不是心软,是怕我会因此与他决裂。可他若真的动了手,我又会拦着吗?或许不会,只是我不想在亲亲家园那样的地方,让自己仅剩的体面碎落一地,所以远远发了条信息让他离开,JZH才得以安然无恙。
这半年里我发的每一条朋友圈,都是精心设计的假象,只为给列表里的人营造“我不能没有JZH”的错觉。所以分手时,我在朋友圈复刻了痛不欲生的模样,向共友打听他的动态,让共友旁敲侧击他的想法。
他果然入了局,以为我是真的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还在朋友圈写了长长的信,搞着隔空投送的浪漫戏码,盼着我能看见。他演得那样投入,可我早已没了配合的兴致,草草写了六行字便停笔。
那时我已经加入了悟空体育,身边有了新的交集,有两个男生真诚地向我靠近,我终于有了勇气跳出那场消耗自己的戏。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虚假的表演,而是一份真正懂我、惜我,能容纳我所有情绪起伏的感情,JZH这样的人,从来都不在我的期待里。
如今再想,这段持续了半年的纠缠,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荒诞的笑话。他演了半年深情,我陪了半年敷衍,这场戏终于落下帷幕。
他或许还沉浸在“深情被负”的自我感动里,却不知道我早已把这场戏当成了一段麻木时光里的消遣。
只有我自己清楚,戏的背后,是我十三年与重度抑郁症、双相障碍抗争的煎熬,是我对感情从期待到麻木的绝望。我不过是借着这场虚假的陪伴,熬过一段不敢独自面对情绪崩溃的时光罢了。
如今戏散场,我该重新回到自己的战场,继续与情绪对抗,也继续等待一份真正值得的温暖。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