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线直击|躯体之痛下的情绪黑洞:那些被疾病偷走笑容的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聪聪 刘通
当帕金森病让身体不再灵活,当化疗药物把肠胃搅得翻江倒海,当血液透析让生活难再自由——在躯体疾病的阴影里,情绪的黑洞开始渐渐吞噬内心:有人悄悄退出朋友群,只因不想被看到拄拐的模样;有人整夜盯紧天花板,担心下一次猝死;还有人把药片攒成小山,想着“长痛不如短痛”……
“综合性医院约三分之一的住院患者会合并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焦虑障碍或抑郁症。”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八科副主任医师孙萌萌说,比起有形的躯体伤病,无形的情绪障碍更为隐匿,甚至可能发展为难以修复的沟壑。

(孙萌萌在病房内与患者交流)
陷落
“我好不了了”
“你们快去楼下看看,有人在欺负银城。”听到这样的呼喊,李玲锁着的眉头更紧了。她不是担心“被欺负”的银城,而是眼前的老伴儿。
银城不是孩子,他是已过七旬的金城的弟弟;银城在家好好的,也没有像哥哥说的那样受到了别人的欺负。这些,不过是金城的幻觉。
4年前,金城确诊了帕金森病。起初,只是偶尔不太受控的震颤,金城还打趣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从去年开始,伴随病情进展,越来越僵硬的步伐悄悄拽着他的生活往下坠。
曾经性情温和、通情达理的老人,开始变得郁郁寡欢,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嘴里反复嘟囔着“好不了了”。
情绪积压,痛苦找不到出口,金城开始自己伤害自己。每次撞见,李玲只能慌忙上前拉住他的手,但是,一个不注意,转身时依然会看到那被打到肿起来的脸颊。
逐渐地,金城开始起“担心”住在楼下的弟弟银城,比如“被人打了”“在楼下摔倒了”,不断要求家里人去看看。家人反馈的信息不放心,他就颤颤巍巍自己下去,反反复复。
直到这一天,李玲和家人商量后,把金城带到了医院。这一次,他们看的是精神科。
张霞的入院和金城一样,也是疾病带来的情绪问题。
因为之前血糖指标控制不好,医生调整治疗方案后,张霞就陷入对低血糖等突发状况的担忧,情绪一直高度紧张,稍微感觉不适就赶紧往嘴里塞糖块儿。
焦虑是得到了缓解,但意外的糖分摄入又影响到血糖水平,进入迁延不愈的恶性循环。后来,她不仅对治疗失去信心,还添了新毛病:胸口总像被什么堵住,喘不过气;身体忽冷忽热,去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医生说,这是典型的“躯体化症状”,根源在情绪里。
困境
躯体疾病催生情绪黑洞
“外科疾病一般能通过手术、药物等方法,相对明显和高效地让病人察觉到治疗的效果,但很多内科疾病是慢性病,治疗预后无法立竿见影,患者需长期承受身体不适,也就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孙萌萌介绍,金城和张霞都是因躯体疾病折磨而出现负性情绪的典型患者。
一组数据更直观地揭示了这种关联:在综合性医院,约1/3的住院患者共病精神障碍,其中抑郁症12%~20%,焦虑障碍8%;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更容易伴发焦虑/抑郁或躯体化障碍,包含帕金森病、癫痫、疼痛、肿瘤、心脏疾病和脑血管疾病等。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老年医学科/保健医学科-神经内科主任贺燕介绍,几乎全部的脑器质性和躯体疾病均可伴发精神障碍,尤其是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比如阿尔茨海默病、自身免疫性脑炎、帕金森病等,是以精神行为症状作为核心临床特征。这类症状不仅直接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更会形成 “症状干扰治疗”的恶性循环,增加原发疾病的诊疗难度,甚至导致预后恶化。
“几乎全部的癌痛患者都会经历焦虑或抑郁状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疼痛科主任贾明睿见过太多被疼痛和情绪双重折磨的人:中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往往不是“忍忍就过”,需要干预和治疗;临床中,常有患者疲惫地说“不想这么活了”“不想拖累家人”。
子宫内膜癌患者赵华的绝望,就来自这种“双重打击”。
从确诊子宫内膜癌到后来肿瘤发生转移,难以承受的疼痛本就让她整夜失眠,出现胸腹水后,氧气流量开到最大仍感觉无法呼吸,这让她原本就脆弱的意志更加雪上加霜,一度想过了结生命来终结这些痛苦。
贾明睿介绍,疼痛带来的生理不适,会削弱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反过来,焦虑抑郁的情绪又会在大脑皮层放大疼痛信号,形成“痛得更凶-情绪更差-痛得更凶”的循环。也是因此,在他开出的癌痛治疗药方中,抗抑郁/焦虑的药物多在其中。
绝望
难以承受的“身份”丢失
孙萌萌介绍,糖尿病、帕金森病等慢性疾病常伴随慢性炎症反应,炎性因子会影响5-羟色胺、多巴胺等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分泌与代谢,直接改变大脑功能。
一些慢病还会导致大脑结构改变,因为人体内一部分控制躯体功能的结构与情绪调节中枢重叠,因此一部分慢病患者的情绪会随病程发展出现负向变化。
对于肿瘤患者而言,这种情绪的变化幅度更大更明显。一方面,疾病本身带来的疼痛会消耗患者的精力,影响他们的睡眠与食欲;另一方面,治疗药物中也可能含有引发或加重负面情绪的成分,进而加剧情绪障碍。
除了看得见的生理原因,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把患者推向情绪黑洞——“社会角色”的突然断电。
能干的妈妈拿不稳锅铲,单位的顶梁柱连签字都手抖……从“我还能做什么”变为“我什么都做不了”,患者首先哀悼的不是身体的变化,而是因疾病失去的“身份”。
“疾病带来的不仅是病痛,还有社会功能的受损。”孙萌萌说,社会角色的变化,会让患者不经意间就萌生出自我否定心理。一旦疾病恶化、治疗失败、高额花费,又没有及时的心理支持,“活着没意义”的无望感就会滋生——而这种无望感,正是自杀意念和行为最危险的导火索。
突围
需要专业治疗与温暖托举
然而,情绪黑洞很像宇宙空间的黑洞,一旦不幸陷入,仅靠自己的力量几乎不可能逃离。
“社会上很多人会把抑郁症看作‘矫情’,觉得患者之所以会情绪低落,就是因为整天胡思乱想。”孙萌萌说,心理疾病与躯体疾病一样,一旦确诊,仅靠家人的“振作起来”“别瞎琢磨”等语言支持,很难帮其摆脱内心的痛楚。
“心病既需要心药医,也需要真正的药物和系统的心理治疗才可以。”孙萌萌补充。“在帮助金城老人治疗的过程中,我们除使用常规药物控制帕金森病症状外,还通过抗抑郁药调节他的神经递质,以改善情绪,同时开展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治疗等心理与团体治疗。从老人自身与家属一起入手,大家一起帮老人拉出情绪黑洞。”
除了精神专科医院的系统治疗,家庭内的情绪补给同样重要。
作为家人,在照顾患者身体的同时,也需要提供积极的安慰与宽容的环境。“家人可以适时帮助患者寻找能获得成就感的事、培养兴趣爱好。”孙萌萌说,很多人在向家人传递情感时,都表现得比较含蓄,并且更倾向于语言上的表达。但对于情绪低谷的家人,有时肢体上的接触,能够给予更强大的心理支持。一个拥抱,或许能胜过千言万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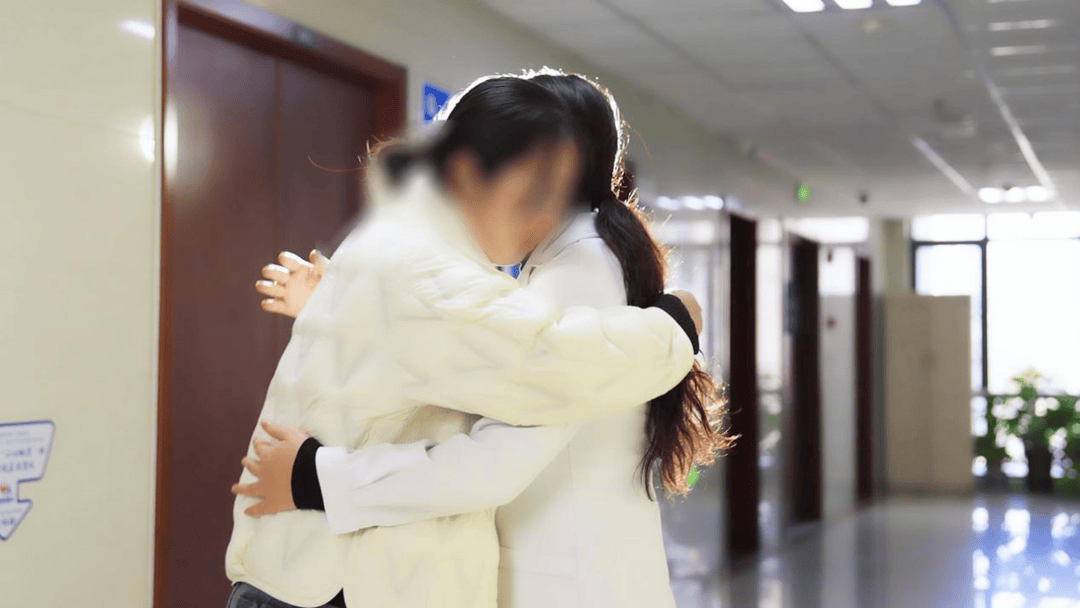
疾病或许能夺走健康,但不应夺走人对尊严与温度的渴望。一个理解的拥抱、一句“我陪你”,或许就是穿透黑洞的光。(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